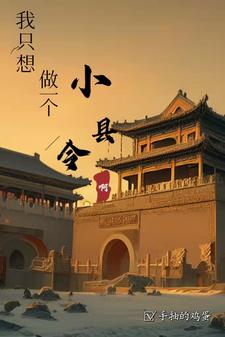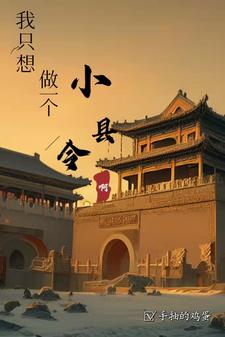
大明:我只想做一个小县令啊
手抽的鸡蛋 著
类别:历史军事 状态:连载中 总点击:100 总字数:2934117
【历史爽文,追求爽点,历史考古就不要进来了,不要太认真!如果错了都是狗作者的错! 生活不易,留个五星】\n “大人!咱们凤阳在您的治理下,百姓安居乐业、粮食丰足,海河清宴,可您为何要连年报灾啊?”\n “你懂个屁!本官还想多活两年呢!”\n洪武二十五年,太子朱标薨逝,朱元璋伤心之余,又必须为未来大明王朝的继承人做出抉择的时候,苏谨来到了这个世界。 \n这既是一个辉煌的时代,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。\n成为朱元璋治下凤阳县的父母官,苏谨不知这到底是祸是福? \n面对洪武二十六年那即将发生的,洪武四大案最后一个牵连甚广的蓝玉案,还有几年后的靖难之役,苏谨只能瑟瑟发抖的躲在凤阳,发誓和谁也不要扯上关系。 \n可命运真的会如他所想,让他这么轻易的置身事外吗?\n这大明皇朝的继承人,究竟是皇太孙朱允炆,还是那朱允熥? \n靖难之役还会发生吗?朱棣又会如愿再次成为永乐大帝吗?\n苏谨不知道,他只知道自从朱元璋带着那几个孙子,来凤阳转了一圈后,一切都变得身不由己了...
https://www.bok360.cc/book/1892989985232646144.html
第1章 升官?升天还差不多
www.bok360.cc
泉眼无声惜细流,
树阴照水爱晴柔。
小荷才露尖尖角,
早有蜻蜓立上头。
夜色弥漫,苏谨手持毛笔艰难地在写着奏折,然而还没过了多久他就选择了放弃。
“该死,都来了三年多了,可这毛笔为什么还是这么难用?”
看着奏折上歪歪爬爬的字迹,他的嘴角忽然透出一抹玩世不恭的笑容,而这抹笑容很快就被苦笑替代。
忽然想起了什么,他立刻冲着窗外大喊:“根生、根生你在不在,你快来!”
“二叔,你叫我?这就来了!”
门帘被轻轻掀开,一个年近三十,面色微微有些苍白,透着一股书卷气的男人走了进来:
“二叔,你叫我?”
苏谨面露嬉笑,语气中却透着些许焦急:“乖侄子,你赶紧过来帮我瞧瞧这奏折。”
苏根生挠挠头,语气中却透着一丝无奈:“二叔啊,按辈分你是我族叔不错,可你毕竟比我小十岁啊,能不能不要老是叫我乖侄子?”
苏谨嘿嘿一笑,直接把桌上的奏折团吧团吧扔进纸篓,然后将一份新的空白奏折摊在桌上:
“好的乖侄子,你赶紧过来坐好,咱们还是老规矩,我说,你写。”
“诶。。。”
苏根生见怪不怪地答应一声,熟练的净手,然后恭恭谨谨端坐在桌前,抬头认真的看着苏谨。
苏谨想了想,努力的拼凑着肚里为数不多的词汇,慢慢开口:
“嗯...先这么写——‘洪武二十五年闰四月初旬,连日倾盆大雨,各处山水暴注,同时暴涨,以致冲决堤堰淹没田庐。
或因河流漫淹,或被山水冲刷,本县被淹村庄自数村至百余村,坍塌房屋自数十间至数百间,压毙人口自数口至数十口,均各轻重不等...’”
苏根生为难地瞧着苏谨,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,苏谨直接乐了:“有话说,有屁放,瞧你那便秘的样子。”
苏根生犹豫地挠挠头:“二叔,咱们凤阳县自三年前开始,在你的带领下修堤筑坝以后,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洪水漫田之事,你不向朝廷表功也就罢了,还频频报灾,这又是何苦?”
苏谨闻言不答,眼神深邃而明亮,明明一张俊朗白皙的脸,不仅没有丝毫的秀气,反而处处透着一种坚毅和自信。
但他一张嘴,立刻就让苏根生想起了县东头的张屠夫:“废他娘的什么话,我是县令还是你是县令?让你怎么写就怎么写!”
苏根生摇摇头,无奈的执笔继续写下去,只是他那一边写奏折,一边犹如便秘一般的样子,苏谨忍不住再次哈哈大笑。
瞧了一眼苏根生的字迹,苏谨满意的点点头:“嗯,不愧是秀才,这字迹可比咱的强太多了,来来来,继续往下写——‘
洪水之初,臣为保祖陵王气不泄,亦遵洪水不没祖陵之嘱,无奈首虑祖陵,次虑运道,再虑民生,唯决水堤放水,然天灾人祸实难避也。。。’”
苏根生的脸彻底绷不住了:“二叔,祖陵明明好好地,你也没有决堤放水去淹百姓的农田啊,反而这两年在你的治下,百姓再无洪水、旱灾之苦,为啥要这么写啊?
况且,你好歹也是进士出身,可为什么自三年前开始你的字就变得那么...那么...难以捉摸?”
苏谨翻个白眼:“你直接说我的字是狗爬的不就行了?”
苏根生嘿嘿一笑,挠了挠头不敢作声。
“我不是说了吗,三年前我脑袋受了冲撞,之后我的手就有些不太听使唤了,没办法写字”,苏谨没好气又略带心虚地瞟了他一眼,赶紧岔开话题:
“这奏折明早就要发呢,你再这么啰啰嗦嗦的,啥时候才能写完?”
瞧了瞧笔下的奏折,再看看苏谨,苏根生总觉得很委屈:
“可我就是搞不懂啊,你为啥就不愿意上书表功?
要知道凤阳县这些年在你的治下,那可是天翻地覆的变化,陛下要是知道了,肯定会升你的官啊!到时候咱光宗耀祖难道不好?”
“你快闭嘴吧!”
苏谨没好气的翻个白眼:“升官?升天还差不多!”
知道不解释清楚,这倔驴一样的木瓜脑袋,恐怕几天都睡不好觉。
不过好在苏根生本是自己本家的亲亲侄子,为人也忠诚可靠,苏谨决定还是向他解释一下:
“我问你,咱这位陛下这些年杀了多少官员?”
“这...”苏根生挠挠头。
“我来回答你,远的胡惟庸案、空印案不说了,近一点的就说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,自六部左、右侍郎以下,就宰了数万人!
有的省份官员几乎都快被杀绝了,这时候你让我表功?那是急着升官吗?赶着去投胎还差不多!”
苏根生微微一滞,惊愕的看向苏谨:“所以这些年,你才刻意疏远府衙的那些官员?”
“是啊”,苏谨叹口气,瞟向了窗外的夜空,眼中似乎带着一丝对过去的怀念。
还有许多话他没敢对苏根生说,因为说出来他也不会信。
就算苏谨并不熟知历史,但是洪武四大案他还是清楚的。
今年五月太子朱标薨,举国哀悼,而远在南京的老朱在明年,就会悍然发动最后一个大案——蓝玉案!
蓝玉案后,也彻底宣布淮西的武勋势力被清除,而他那可爱的皇太孙朱允炆,也能安安稳稳的上位了。
自己这个时候往上爬?
那和找死有什么区别?
万一不小心牵扯到哪个大佬的派系中,到时候恐怕自己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
更何况,将来还有一出更刺激的大戏要上演,苏谨可不想作为老朱或小朱的‘前朝欲孽’,被那位大帝拎出来宰了给他助兴。
“二叔,那接下来的奏折怎么写?”
苏根生虽然懵懵懂懂的似懂非懂,但是自己一向信任这个年纪比自己小的族叔,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
“哦哦。”
回过神来的苏谨,想了想继续念道:“地力既尽,元气日销,天灾流行,人事屡变,田上则者,归之军,归之功勋矣。
中则者,土民括其一,佃户括其一,惟留下则处瘠,乃得以实编民之耕。”
苏根生一边照着写,一边想着田地的金黄和谷仓的丰满,嘴角不由得直抽抽,但终于没再提出异议。
看着苏根生落于纸上的字迹,苏谨一脸得意:“我他娘真佩服我自己,你瞧瞧,我哭穷的时候顺便还能再告上那帮子老勋贵们一状,
老朱啊老朱,你看到奏折以后可要明辨是非啊,我跟他们可不是一伙的,砍人的时候千万别捎带上我,阿弥陀佛。”
满意的点点头,苏谨忽然问道:“乖侄子,户籍这边一直是你在管着,现在凤阳县有民多少户啊?”
苏根生慢慢放下笔,认真想了想后说道:“三年前咱们凤阳县本来还有三万多户,后来逃走了不少,只剩下不到一万户,
不过自从二叔你上任以后,招徕流民安户,如今已恢复到两万户左右。”
“嗯...”
苏谨想了想:“那就这么写吧——
群趋于惰,兼之水旱频仍,中人荡产,且乏兼岁之储。一遇灾荒,辄膏子女、弃故土而适他乡者,比比皆是,今县中逃剩不到万户。”
这次苏根生连嘴皮子都没抽一下,老老实实一字不差的写了上去,反正就是按照实际情况反着写呗。
无他,唯手熟尔。
第2章 不争
www.bok360.cc
“盗匪横行,然县中无可用之兵,兵甲破损已久,多有溃烂,士兵粮饷欠发已久,苦无战心...”
“...乃至县周处处盗贼横行、民不聊生,商人闻之无不远避,京凤之驿路,年久失修,于数百里间,破败处处,甲第无相望,
行商宁绕道而行,亦不愿在此落脚,可谓苦矣,城中商户处处破败,粮价飞涨,售粮商户却禁闭大门,不见其踪...”
念到这里,苏谨忽然想起什么:“对了,姓王的那混账今年的税交了没有?”
苏根生微微一笑:“交了,自从去年你狠狠收拾了他一顿,让他赔了十数万钱后,他现在可是老老实实的纳税,今年还是咱们凤阳县的纳粮大户呢,今儿个才命人把锦旗给他送去。”
想想自己亲笔提的‘纳粮先锋’几个爬爬字,苏谨就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声来,也不知那姓王的敢不敢挂出来。
“行了,大概就这么多了,乖侄子你瞧着再给润色一下,叔叔我先去睡觉啦!”
“桃红,桃红,冰盆给老爷置好了没有?”
门外传来一声清脆的女声:“回老爷的话,按老爷的吩咐,冰盆一炷香前就放到您卧房了。”
“得嘞~~我去也!”
留下一脸苦笑,连夜改着奏折的苏根生,苏谨晃晃悠悠的回了自己的卧房。
坐在宽大的书桌旁,随手从上锁的抽屉里取出一本书,摇头晃脑的看了起来。
明亮的烛火照在书的封面上,‘军地两用人才之友’几个字被照的阴晴不定。
装模作样地瞅了几眼,苏谨忍不住打了个大大的哈欠,然后蹲下身将冰盆搬到一个离床更近的位置,随手将外衣解下扔在一旁,懒洋洋地躺到了床上。
“哎,没想到一转眼都来了三年了,可这该死的系统怎么还是那个鸟样子?”
苏谨本是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一个普通人,普通的学业、普通的工作、普通的生活、普通的婚姻。
哦,婚姻并不算普通。
他是在洞房花烛夜最开心的那一刻,不知是因为太兴奋了,还是因为酒喝多了,莫名其妙的就来到了这里。
来到了一个和他一样‘普通’的进士,一个普通的穷县县令的身上。
前身也叫苏谨,还有个挺好听的字——慎之,意味着行事必须谨慎。
可就是不知道,这么一个处处小心,行事谨慎的家伙怎么说没就没了呢?
随手触摸着左手无名指,那处隐约带着淡淡痕迹的纹身,苏谨意识陡然一晃,又回到了那个这三年来他无比熟悉,却没有丝毫变化的地方。
苏谨不知道这算不算他的‘穿越福利’,是不是穿越移民必备的金手指,他只知道第一次发现这个‘系统’的时候,就是这个鸟样子。
与其说他是系统,倒不如说是个仓库,但目前唯独对苏谨开放的,只有一间类似于办公室的房间。
仓库的内部,四周有几道紧紧关闭着的大门,这些年苏谨想尽了任何办法也打不开,只能泱泱放弃。
唯一收获的,就是当时在办公室桌面上摆着的这几本书、
《赤脚医生手册》、《军地两用人才之友》、《民兵军事修炼手册》。
以及一本《教员语录》。。。
靠着这几本书,苏谨勉强用三年的时间打造出了一个不太一样的凤阳县。
只可惜,本以为能继续解锁新的仓库,但这三年来仓库毫无变化,让苏谨怀疑那几个门压根就是摆设。
从仓库中退出,苏谨悠悠地闭上了双眼:“算了,算了,为今之计还是先想办法苟过这几年再说,至少朱棣上位之前自己可不能作死...
不过话说回来,杜知府这个月的份子,可得赶紧差人送过去了,咱还指着他替自己隐瞒一二呢...”
想着这些烦心事,苏谨沉沉的睡去,不知道梦里是不是回到了自己的那个时代,嘴角慢慢噙起一丝微笑。
不久之后屋内鼾声四起,他的眼泪不争气的从嘴角流了下来。
“唔唔,老婆,你别急嘛,待为夫先热个身...”
这是一个没有被光污染的时代,漆黑的夜空中繁星点点,照耀着熟睡中的苏谨,同时也照耀着南京皇宫中那位不幸的老人。
朱元璋冷着脸,多年的帝王习惯,已经让人从表情上看不出他的任何心情,但是眼底不时流露出的一丝悲戚,映照着他此时悲凉的心情。
他最爱的儿子,自己心中大明帝国最好的继承人,就这么永远离开了自己。
他才三十七岁啊,正是年富力强的好时候,怎么就这么走了。
朱元璋有时候忍不住想,若是自己能替他死去,想必也是心甘情愿的吧?
但这一切随着朱标离开,都不过是设想罢了,目前摆在朱元璋面前的还有一个难题——下一任大明的继承人应该选谁?
橚儿?棣儿?
还是...
朱元璋忍不住蹙了蹙眉,用手指摩挲着愈发难过的额头:“来人。”
“皇爷,奴婢在”,一个五十岁许的老太监匆匆从殿门口小步跑进来:“皇爷,您有什么吩咐?”
朱元璋瞧了一眼,认得是近侍马忠良,缓缓开口问道:“炆儿最近怎么样?”
马忠良想了想,低声答道:“回皇爷的话,太子殿下走了以后,二爷日夜悲哭,这些日子才稍好了些,今日早早的就歇下了。”
朱元璋不置可否,忽然想到了什么:“熥儿他们呢?”
“三爷前些日子大病了一场,御医们给调理了一番,倒是没有大碍。”
朱元璋微微点头,心里对朱允熥有些愧疚。
长孙朱雄英早夭,太子妃常氏产下朱允熥后就病逝,可怜这个没了娘的孩子从小被吕氏带大。
朱雄英夭折后,本来他才是真正的嫡孙,但后来太子妃之位不能闲置,朱标将吕氏扶正,老二朱允炆反而成了嫡长孙。
虽然自己更看好朱允炆,但是朝中淮西武勋和浙东文官一直吵嚷不休。
淮西武勋认为朱允熥才是真正的嫡孙,而浙东文官则认为朱允炆才是正统。
但朱元璋在意的,却不是他俩的出身,而是他们的身后。
朱允熥的生母,原朱标太子妃常氏,是常遇春的长女,他身后的外戚关系更是错综复杂,舅舅常升、常茂,舅姥爷蓝玉...
忍不住再次揉了揉眉头,朱元璋似乎下定了决心。
“若是让熥儿上位,这大明江山最后到底是我朱家的,还是他们的?”
想想朱允熥那唯唯诺诺的性子,朱元璋更是不喜。
虽然他也知道朱允熥出生即丧母,从小被吕氏带大,性子难免懦弱了一点,但再想一想,这其实也算是个好事。
懦弱,即不争。
“唉,将来给熥儿封个好地界,让他好好的过完这辈子就是了”。
朱元璋龙目扫过阶下,看到马忠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,冷哼了一声:“有什么话就给咱说。”
马忠良讪笑了一下,低声说道:“回皇爷,郡主前些日子也受了风寒,近日身子好了许多,总是嚷嚷着要见皇爷您呢。”
想起江都郡主朱灵萱,朱元璋的嘴角忍不住抹出一丝笑意。
朱灵萱是朱标的长女,温文贤淑,性子稳重又庄重,颇有乃父之风,尤得自己喜爱。
“嗯,你去告诉萱儿一声,说咱忙完这些公务就去瞧她,让她好好的将养身子。”
“奴婢遵旨。”
批完龙案上的奏折,朱元璋伸了伸懒腰,瞧着外面的夜色,忽然觉得无比的萧索和寂寥。
“标儿的魂不知道是去了哪里,是不是回了祖地去寻他爷爷去了?要不...这几日咱也抽空回祖地看看?”
第3章 你说啥!?这条路是凤阳县令修的?
www.bok360.cc
谴退了马忠良,朱元璋在心里认真的考虑起了回凤阳祖地的事情。
“这次回祖地,炆儿得带上。”
他又想了想:“算了,熥儿也带上一起去吧,熞儿也大了就一并带上吧,熙儿还太小就算了。”
想想爷孙一同出游的画面,朱元璋嘴角忍不住浮出一丝微笑,眼中更是漫出了少有的温情。
突然想起了什么,朱元璋从一堆奏折中翻翻找找,终于从中找出了一份来自凤阳县的奏折。
可当他打开之后,眉头忍不住深深地皱了起来:“祖地的百姓,当真过的如此困苦吗?那县令是做什么吃的,犹如酒囊饭袋一般,当真该杀!”
要是苏谨知道,自己‘哭穷’的奏章被朱元璋看到后,居然因此动了杀心,不知道会不会哭晕在厕所。
不过朱元璋对苏谨显然并没有太过在意,杀不杀区区一个凤阳县令,对他来说不过是一句话的事,他心中忧虑的还是凤阳百姓的日子。
前些年他为了造福凤阳,差点没把京城都搬到风阳去,要不是群臣力谏,再加上刘基上书,朱元璋还真准备迁都,把凤阳变成京城。
迁都之事虽然不了了之,但他对凤阳依旧不遗余力,更不惜财力、物力,强制迁徙百姓移居凤阳,并减免税赋、改善水利,并将凤阳定为中都。
可谁能想到随着这些年过去,凤阳不止没有变得更好,反而变得越来越差了?
一定是那些官员不作为!
朱元璋决定这次回去,要借这次机会好好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,那里的官员是不是尸位素餐?
若是被自己发现有人贪婪无度、玩忽职守,那就别怪自己心狠了。
“哼,要是让咱知道了,一个也别想跑!”
朱元璋是个行事十分果决的人,第二日一早将宫中的事情安置妥当之后,带着朱允炆、朱允熥、朱允熞,以及江都郡主朱灵萱微服离开了京城。
车声粼粼。
南京通往凤阳府的驿道上,一辆马车在缓缓向北行驶。
第一次出门,车上的四个孩子难掩对外面世界的好奇,时不时将脑袋从车窗伸出窗外,看着窗外的景色。
南方的六月骄阳似火、闷热如荼,马车内尤其格外的闷热,朱元璋一边看着手中的奏折,一边皱着眉头擦汗。
朱允炆小心地在一旁伺候着,瞧着朱元璋的神色忍不住问道:“皇爷爷,您怎么了?”
朱元璋面露慈爱之色,轻轻抚了抚他的脑袋,叹口气说道:“咱看着这些奏折,心里委实有些难受,没想到大明立国都二十多年了,凤阳祖地的百姓生活依然这么困苦。”
朱允炆想了想:“皇爷爷,孙儿觉得应该严查一下这凤阳府的官员,看他们是不是不作为。”
“是得查查”,朱元璋冷哼一声,想起凤阳县那个县令的奏折,心中就尤其恼怒。
马车很快就离开了南京地界驶入了凤阳。
朱元璋在车内靠着车厢昏昏欲睡,可忽然觉得哪里有什么不对。
“停车!”
赶车的是湖广行省左丞周德兴的儿子周骥,也是朱元璋比较信得过之人,这次微服出行扮作车夫,实为护卫。
周骥闻言急忙将马车停下,恭敬的跳下车慢慢掀开车帘:“陛下。”
朱元璋扫眼望去,果然前方是一条宽阔笔直的大道,不知是由什么修成。
朱元璋刚刚觉得不对,就是因为从南京出来上了驿道后,一直坑坑洼洼、颠簸不已,可现在居然平坦舒服的让自己想要睡觉?
“这条路是怎么回事?”
周骥也不清楚。
这条路也是忽然变得好走的,他刚刚还感叹这凤阳县不愧是祖地,路都修的比别处好。
如今皇上问起,周骥只好道:“臣去寻几个百姓问问。”
“不必了”,朱元璋看着道路两边金黄的田地,心情忽然变得好了起来:
“咱在车里也坐累了,正好四处走走。”
话音刚落朱元璋就下了车,他背着手,一边欣慰地瞧着即将丰收的田地,一边纳闷:
“奏折上不是说‘地力既尽,元气日销,天灾流行,人事屡变’吗?为何放眼望去皆是一副丰收的景象?”
不由得心里暗骂一声,此县令必然从不出来堪舆民情,定是个大大的昏官、贪官、懒官、庸官!
朱元璋身后,几个孩子也跳下了马车。
已经十五岁的朱允炆,心智早已成熟,此刻他正熟练地拿着折扇,跟在朱元璋身边为他扇风,驱走酷暑的闷热。
而十四岁的朱允熥,虽然有心想要上前尽孝,可看到二哥已经抢先一步,只好唯唯诺诺地跟在身后。
朱允熞才七岁,没那么多的心思,开心的蹦下车来,一边喊着‘皇爷爷等我’,一边追了上去。
朱元璋脸一板:“熞儿,说了几次了,咱出来可是微服,出门以后只能喊我阿爷,不许喊皇爷爷!”
朱允熞扮个鬼脸:“知道啦皇,不,阿爷!”
朱元璋瞧了一眼停在道边的马车:“萱儿怎么还不下车?”
车内传来一声娇俏的女声:“孩儿是女子,为防礼法不敢下车。”
“屁的礼法!”
朱元璋不屑地翻个白眼:“在咱这里,咱就是最大的礼法,车里那么闷热待着作甚,赶紧下车透透气。”
“是,阿爷。”
周骥赶紧上前小心翼翼地伺候着。
这次出门,陛下点名命自己护卫,连锦衣卫都没带几个,足以说明对自己父子的信任,可一定要尽心尽力,博得陛下欢心才是。
江都郡主朱灵萱莲步轻移,借着周骥准备好的马凳慢慢下了车,露出一张倾国倾城的脸。
此时的她虽然年方十四,很多地方还没有完全长开,但那白皙如雪的肌肤、宛如玉雕般的面庞,已经能看出是一个十足的美人胚子。
朱灵萱下车之后,眼睛四下打量周围的环境,若秋水一般的眼眸中露出好奇的表情。
有心想找皇爷爷说说话,可发现朱元璋早带着朱允炆和朱允熥下到了地里,和农人们聊的火热。
朱允熞嫌闷,甩开了膀子在地里飞来奔去,玩的不亦乐乎。
朱灵萱有心想下去,可瞅了瞅地里的一群人,旋即放弃了这个想法,叮嘱了一句朱允熞不要踩坏了农家的地,就悄然站在一边欣赏起了风景。
而此时朱元璋看着眼前的农人们,露出一脸大惊失色的表情,急得连老家话都蹦出来了:
“你说啥!?这条路是凤阳县令修的?”
https://www.bok360.cc/book/1892989985232646144.html